本篇文章2701字,读完约7分钟
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叫王的。一米宽,能跳过去,水深只有脚的肚子那么深,但出水时没有膝盖。至于长度,我只知道来源,但目的地没有测试。平凡,平淡,平凡到没有名字。这是深圳村民的意识。似乎太阳底下什么也没有留下,但是深圳的这一段,从源头往下500米,让我读到了这一点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我的父母抱着我的小胳膊,指着我的“深圳-深圳-深圳”的胡言乱语。当你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,你经常会不由自主地爬到深圳。深圳的水流清澈欢快,涟漪呈箭头空的形状,一个接一个地堆积在一起,推动着波浪向前。深圳底部光滑的鹅卵石和细沙混合在一起。深圳岸边的野草和野花随风起舞,它们的倒影流动而优美。

小时候,一群裸体伙伴喜欢在深圳玩耍,争水,在海浪中追逐白色的栅栏,自己做纸船或捡几片竹叶让它们浮在船上,向过往的女孩泼水。年龄相仿的人用手捂住脸,侧身哭着躲开他们,而年龄较大的人则喊着“坏男孩和臭男孩”。我们绝望了,我们到处乱跑。即使透过深圳银行的鸡、鸭、狗和猫,我们也无法逃脱疯狂玩耍的恶作剧。当我们看到鸡在飞,狗在跳的时候,我们是“幸灾乐祸”和快乐的。也许浅水区不担心安全,干净的水可以清除污垢。面对这些不守规矩的行为,大人已经习惯了,一般也不会去注意它,这样我们就能享受到孩子的乐趣和快乐。

深圳的流动是无止境的,何时,由谁?因为没有名字,所以没有书面记录。不幸的是,长老们不知道为什么。然而,源头和流向清楚地表明,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,U型水系闪耀着先人实践自然思想的光辉。小明池塘形成U形的底部。小明池塘不小,水面近20亩。荷花每年都盛开,优雅美丽。西干渠在右边,发源于100英里外的九步江水库。它沿着连续的山坡从西北向东南延伸。该村预设有引水涵洞,通过落差和涌水将引水涵洞注入小明池塘。深圳在左边,水从唐晓明坝基的涵洞流入。“U”形水系覆盖沃野农田,有彩色的草籽花、黄澄澄的油菜花、小颗粒大小的白米花...一年四季随着节奏起舞,散发着芬芳。

甘熙运河是在解放后修建的,其流域没有干旱的危险,只是在淡季水库被切断了。即使运河被切断,深圳河仍然日夜不停。在唐晓明的历史上,堆积的雨水和涓涓细流都是从它腹部后面的山田里涌出来的。深圳河是我家乡的命脉,基本农田的灌溉、菜地的灌溉、家庭的洗涤、牲畜和家禽的饮水,这些维持生命的一切都要靠她。据我父亲说,1963年,历史上最干旱的一年,只有小明池塘下的稻田有了收成。如果池塘里没有水,整个村子都会饿死。

深圳下游,左侧地势较高,为倾斜的旱地,只能种植红薯、蔬菜等旱地作物,右侧地势较低,到处是稻田。唐家场,祖籍,是一所大房子。它位于深圳的左侧,是根据深圳的情况建造的。它分为三个生产团队:上院,中院和下院。从深圳的边缘到内部,房屋与地形相接。上、中、下三层房屋依北斗七星延伸,长约500米,居住着300多人。上屋的形状像北斗七星的勺底,中屋像勺柄一样与下屋相连。生活在水边,民俗简单而舒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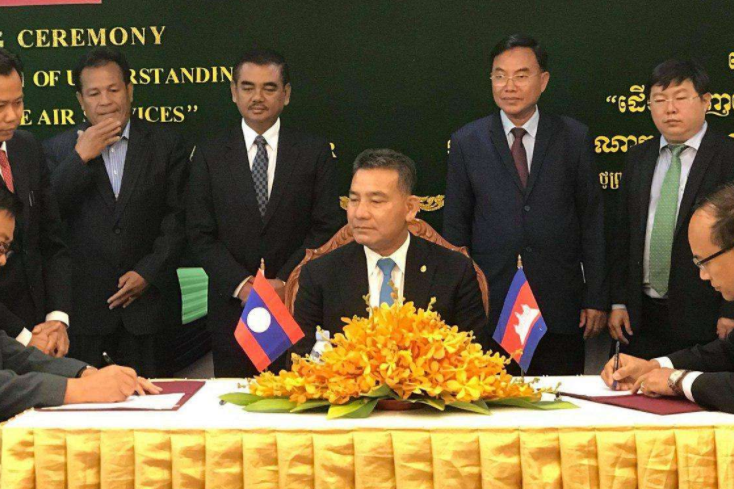
我家属于的那栋楼上的房子是最华丽的。房屋庭院形状良好,纵横交错,错落有致,浑然一体。它由一个巨大的十字形大厅连接,阳光充足,没有阳光,潮湿得足以从一个房子走到另一个房子。大门前的禾坪很宽敞,用淤泥和石灰建造。禾坪前面的一个方形池塘叫做武门池。武昌的和平水库在深圳的右边。打铁的时候,打棉花、做木工、杀猪、唱戏、设宴都在大厅里进行。在禾坪,收获季节晒晒玉米和薯片,假期玩玩杂耍和舞龙。这里人来人往,人缘最旺。青石板桥位于深圳,铺在房子内外的主干道上。

深圳像楚江和汉朝一样,所以民族居住区和劳动区有着明显的区别。成员们听着船长的哨声,在田野里耕作。他们下班回来后,习惯性地在深圳洗脸洗脚,洗掉工具上的污垢。孩子们带着书包去上学,老人看着耕种的收获。一家人期待着旅行者的安全归来,小贩们挑选了他们的包,并进行买卖...

在那个没有电灯的时代,夜幕降临,村民们都坐在长凳上,聚集在深圳的边缘,骑着凉风,听着流水,闻着富饶的庄稼,看着天空空月亮和大海空聊天,我经常沉浸在其中,我被当地的条件,当地的法规和人民的协议,和农业文化所感染。我听过多少次祖先能够保护农村的英勇事迹和轶事?年轻的头脑变得越来越开明,天道酬勤、知识改变命运的原则正在不知不觉中成长。

锣鼓声宣布了一场全面展开的园艺运动的开始。在宽阔的山脊上,红旗在风中飘扬。挂在广播杆上的扩音器不断播放革命歌曲和战斗口号。将全镇的劳动力聚集在一起,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战斗,真是壮观。几个月后,荒野中的农田变得大小一致,深圳的排灌功能明显增强,这也为机械化耕作创造了条件。第二年,全面提高西干渠水位的战斗又开始了。事实上,一条流向相同的西干运河被重新挖掘,绵延数百英里,银色的锄头在飞,提着篮子和梭子,夯歌和夯土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传来。只有一个寒假可以完成,肥沃的土地将增加一千公顷,土地将被播种。大约在1970年,这两次伟大的战斗让我童年时很开心。

第一次来到深圳的青少年,也就是加入了在深圳耕种农田的劳动大军。在秋收季节,热闹的劳动场面对年轻人来说是最激动人心的。半工半读的插秧和插秧正在争先恐后地相互追赶,打谷机的轮子随着所有的劳动轰鸣着飞起来。篮子里装满了新割下的新谷茬,它们很快就被用杆子送到了禾平。男孩和女孩们兴高采烈,生命的黄金时期正如火如荼,老人充满自豪,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。

当时,虽然村民们缺少肉和油,但没有人打破他们的膳食。深圳水草是我们祖先的生命线,灌溉农田和菜地,滋养水稻和蔬菜,为牲畜和家禽提供干渴。
1980年仲夏的一天,我从一中回到四中。我母校的老师和学生聚在一起比较答案,他们都认为我交了一个好答案。兴奋的心久久不能平静,直到老师提醒我报告好消息,我才收拾好行李,兴奋地冲回家。当我回到家时,我看到了明亮的月亮空,星星布满了天空,青蛙在唱歌和飞翔。远远地,我母亲独自站在深圳河对面的青石板桥上。当她走近时,她母亲用期待的目光凝视着。"儿子,考试怎么样?"你吃过了吗?”“别担心,我儿子一定已经学会了。”我答道,天空映出了光芒,桥下的王镇一片欢腾...

从那以后,我成了一个流浪者,深圳是我的家乡。
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,我的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水稻由机器种植和收割,无人机喷洒杀虫剂。村民的劳动强度降低,生活水平提高。值得称赞的是,在与现代文明的密切联系中,山川保持不变,池塘清澈透明,植被更加绿色,田野里新聚集了成群的白鹳,它们时不时地飞来飞去。

根在哪里,根就在哪里。母亲的眼睛是永恒的,她的乡愁在增长。如今,每次回家,我总是去深圳,弯腰,抓一把水,把鼻子伸进去,再洗一次脸,回味那些日子,享受无尽的甜蜜。
来源:成都新闻网
标题:一汪圳流
地址:http://www.cdsdcc.com/cdzx/8020.html




